金水疑云,剑三如何完成金水镇任务金水疑云?
话说这个任务是说,某女秀茹拿剪刀蓄意杀害了她的丈夫林三…现在就开始…逼供吧~~
1、首先询问秀茹,她说她中午在张屠户那买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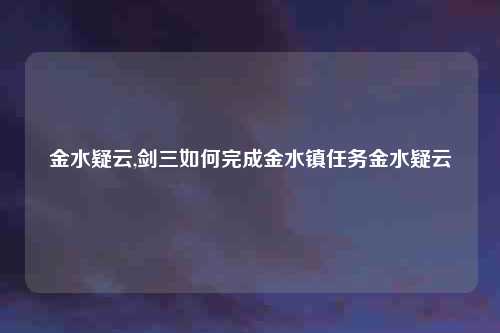
2、询问张屠户,他说中午去帮王氏修门去了没开门,于是叫秀茹去李屠户那里买肉
3、再询问王氏中午在何处,她会告诉你她去林三家时看到满地鲜血,秀茹正被吓地尖叫,而再问她秀茹这个人如何,她告诉玩家秀茹很爱下棋,性格沉着冷静
4、问李屠户,他告诉你中午之后秀茹去他那买过肉
5、好了,千万别忘记最后一个证据哦,找仵作问明他的验尸结果….他会告诉你林三身上的致命伤是胸口的剪刀刀伤,刀口向上,应该是蓄意谋害
6、好啦,最后一步就是质问嫌疑犯秀茹了,先点张屠户的证词,再点李屠户的证词,这时候秀茹会说她是一时冲动才错手杀死自己的丈夫 ,接着点王氏的口供,最后点仵作的验尸报告…于是乎秀茹招供!
雍正王朝里李卫为什么要提醒雍正杀弘时保住弘历?
自古帝王之家为夺位之事大动兵戈,比较著名的是唐朝的“玄武门之变”,为了争夺皇帝宝座父子相疑、兄弟相残、萧墙之内尔虞我诈,以至于后来的康熙朝又上演了“九子夺嫡”的大戏。
雍正凭着办事严谨、不拉帮结派,又有一个好儿子弘历,因此获得了康熙帝的认可,虽然登位过程比较惊险,可最终还是如愿以偿。而接下来他的三个儿子中,老三弘时也窥视帝位良久,而且不遗余力的想获得帝位,上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的武林大戏……
祸起萧墙,为夺嫡千里大追杀“那龟顶峰离这里往返七百余里,又是太平世道。”刘统勋柔声问道,“你怎么敢犯浑到河南劫票?你也忒大胆的了。”
说完偷看一眼弘历。黑无常拭泪道:“那个跑了的铁嘴蛟,他爹在世和我是把兄弟。五天头里上跟我说,有一路镖,肥得很,带的银子有十几万不说,镖主的仇人肯出五十万银子买他的人头。各路人马都调到南北官道上等吃块肥肉,谁劫下来分三十万,其余黑道朋友分二十万。总是我鬼迷心窍,带着弟兄们就下山了……”
“谁——谁出五十万?”
“回老爷,不知道。”
“嗯?!”
“真的!”黑无常抬起头来,急急分辩道,“铁嘴蛟说他也不知道。只说主人来头大极。各路都由一个道士主持,还有一个满口京腔,嘴上没长胡子的老公儿,叫潘世贵,是京里哪个贵人府里开革的。我们这一股把守延津,限期今晚赶到。别的我真的说不上来了。”
弘历听得心旌摇动,已经断然肯定了自己原来的猜想,他想不到平日温文尔雅,揖让谦逊的三哥居然下得这样的辣手,而且不惜动用江湖匪盗沿途设卡,必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已!思量着,已有了主意,突兀一句对黑无常道:“你没有骗我,我也不骗你。我可以赦了你。你想走也可以,想留也成。”
黑无常瞪大了眼。
“我替你想,留在我这里好。”弘历脸上毫无表情,“因为你罪案未消,官府照旧要拿你。你的匪众已全数擒获,回山寨也做不成勾当。你自己怎么想?”
“我愿随爷左右执鞭坠镫!”黑无常毫不犹豫地说道,“不是情极无奈,这年头谁还往黑道上钻?”弘历点头微笑,指着秦凤梧道:“他也是犯了罪,我赦免收留下来的。
看来我还有点功德,你先前杀官劫路,这个罪名儿了不得,要分两步棋儿走。先到密云我的庄子上当个副管家,过两年事情息了,换个名字补到营里,几仗打下来挣个将军副将的,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这么着可成?”
他轻描淡写,为黑无常勾勒了后半世的如花似锦前程。黑无常全身的血几乎都涌到了脸上,心怦怦急跳,几乎要晕过去了,半晌才捣蒜价磕头,只是喃喃一句:“爷是我的再生父母……”
……
衡臣相公,”弘时随张廷玉进了书房,接过丫头递来的茶捧在手里,劈头一句言语惊人:“我不是个爱串门的阿哥。这次老四在河南境内连连遭人毒手,险些送命,是脱难逃回京城,你晓得么?”
张廷玉刚刚端起杯,热水一下子溅在手上,忙放了茶盘时,死死盯了弘时一眼,倒吸一口冷气道:“有这样的事?!田文镜居然不奏,一路过来的滚单,连提也不提!”“那是为了机密。”
弘时声音低沉而又清晰,“详细情形我还不太清楚,老四渡河坐了贼船,在铜瓦渡口上游和水匪周旋了将近一天。附近有打鱼的看见了,报案直到开封府。开封府派人去看,已经是第四天的事,在铜瓦渡口捞上七具尸体,穿着水鬼服装,身带刀伤,刚刚查明这股水匪是个叫黄水怪的领头。
老四许是有高人暗中相助——因为水中打捞那么多尸体,船上还有两具都是匪盗,老四又安然无恙!田文镜的禀帖上来,我立刻下了片子叫查找老四下落,又令李绂送弘历回京。我知道的大抵就是这些了。”
张廷玉久久没有言语,心中极是不平静,这当然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案,从康熙第一次南巡,杨起隆在昆卢院密谋炮打行宫,到现在几十年,天下太平已久。
但同时,张廷玉心中又起疑云:这么大的事,这位办老了事的坐纛儿阿哥竟然不晓得知会自己一声,越过政府就自行秘密处置,是什么意思呢?
李绂和田文镜辖境接壤,二人又正笔墨官司打得火热,偏偏田文镜四面受攻时,可巧就在他境里出了谋害皇子案,这背后有没有别的文章呢?思量着,张廷玉徐徐透了一口气,说道:“阴阳不调匪盗纵恣,乃是宰相之责。我是太大意了。这件事还要直接问问四爷,然后奏明皇上,或由刑部,或交李卫,一定要限期破案。”
“我知道这案子已经十二天了。”弘时扳指算了算松开手,“这不是件体面事——要知道,皇上推行新政,朝野非议得很多。
但我不想惊动朝廷,也不想给皇阿玛添乱,因为与大政无益嘛!”
“四爷刚刚回京,他是钦差大臣,得先见皇上述职才能说到别的上头。”张廷玉自觉至此才明白弘时来意,笑着说道:“您也是奉旨坐纛儿,不奉旨就敢把差使交给别人?倒是李绂那份弹劾田文镜的奏折和田文镜的奏辩,已经发到各部几天了,要赶紧收集大吏们的意见是要紧的。皇上回京,头一件必定要问这个案子的。”
送走弘时,张廷玉看时辰,正是钟响十声。
他只觉得心中烦躁气血不定,虽然弘历的遇险经过尚不详细,但在铜瓦渡口就发现八九具尸体,可见当时情形的险恶。弘历,那是在一百多名皇族子弟中唯一跟着圣祖侍候书房学习政务的,又是雍正儿子里唯一封了亲王的皇阿哥。
张廷玉是亲历亲见过雍正兄弟间争夺嫡位血淋淋的场面的。投毒、截杀、刺杀、设陷于前落井下石于后……无所不用其极——要真的是这样,自己想后半生当个太平宰相的愿心就彻底完了!
他想得头都涨疼了,终归知道的情节太少,得不出结论来。但弘时说的瞒着雍正,这件事却万不可行,漫说田文镜不会隐瞒,连弘时自己也保不定这会子正写密折给皇帝呢!张廷玉那张清癯严肃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铺开纸来,下垂的眼睑一动不动凝注良久,缓缓写道:
奴才张廷玉叩请圣安,敬密跪奏:适才皇三子弘时夜造奴才府……
详细写了二人对话情形,笔触一顿,接着又写道:
弘时敬忠之心,孝拂之情溢于言表。然据奴才思之,兹事体大,长掩亦属非道。惶骇颤栗之余谨陈密奏,并请皇上严加处分,以为大臣疏漏失职之戒。俟奴才与皇四子弘历谈之后,自当另行具折。所请当否,惟圣裁之后奉旨遵办。
写完又看一遍,满意地放下笔,仰身深深打了个呵欠。
张廷玉料得一点不假,他打呵欠时,弘时的密折已经誊清。不过他的折稿不是自己起草,是三贝勒府头号幕僚旷师爷所写,因密折不许代笔,所以由他亲自誊写。
他又仔细看了一遍,和张廷玉折子不同的,前面有田文镜的奏片摘要和自己亲自处置的过程,和张廷玉谈话也略去了,只说“已知会军机大臣张廷玉,钩缉元凶”,其余都是赞誉弘历“颇识大体,雅不欲以己身安危致使皇阿玛焦虑劳心。
观其情形,似日皇阿玛龙体欠安,俟痊好之后徐徐奏知,此亦孝诚之悃,儿臣亦心折感动,黯然涕下矣!”他也打了个呵欠,对守在身边的旷师爷道:“就这样发出去吧!”
“是!”那旷师爷拿起折稿回身便走。
“回来。”
旷师爷站住脚,用询问的目光盯着弘时,没有说话。他是保定人,叫旷清行,年纪不过三十五六,十二岁入学,五进考场乡试,俱都名落孙山。替别人当枪手时却是考一场中一场,索性就以此为生,有名的“旷鸟铳”。
自己秋风驽钝名场失意,代挣的银子却获资巨万。李绂到任访查出来又气又笑,革掉了他的秀才,当笑话讲给张廷玉,却被弘时听了心里,辗转罗致到府里。此人不但文章又快又好,遇事思路也十分敏捷,话不多却简捷明了,只一年间便成了弘时最得用的心腹清客。弘时目光在灯下流移不定,许久才问道:“都掐断了?”
“掐断了。”旷师爷道,“聂公公太扎眼,送到哪里人也能看出他是个老公儿,用的药酒。其余人知道的不多,我们不犯着杀那么多,都打发了黑山庄上,用人看着,用钱喂着——随时都能处置。只有铁头嘴,逃到了山东抱犊崮。其实,他一个土匪,知道的也不多,坏不了爷的事。”
弘时阴着脸又思索一会儿,摆手道:“买通抱犊崮的黄九龄,除掉!一个后患也不可留——你去吧!”
高人提醒,无奈走得太远弘时迟疑了一下,拽着步子回到韵松轩,果见贾士芳一身黑缎袍褂,头上戴着瓜皮帽,腰里玄色带子,脚下一双冲龙千层底靴子,正站在自己案前看邸报。他加快了步子,一进门就笑道:“老贾,你这牛鼻子,穿这一身像一团黑炭,又配着这张白脸没点血色,活像个无常。方才见了十七爷,他一脸的不喜欢,十三叔身子不好么?”
“十三爷大限已到。”贾士芳神情悒郁,冷森森说道,“我这一身就是吊他的,倒是三爷这‘无常’二字说得好。就是帝室贵胄,王孙公子,福命滔天,也毕竟有用尽之时。愈是养德惜命,不敢稍微妄为,上天才肯将全福全寿赐予他。三爷您说对么?”
弘时一笑坐了椅上,把玩着一方玉石镇纸,说道:“后唐时节皇帝求长生,宫中养活多少异能道士,自古痴人多,毕竟也没见着个真神仙。像你,也只是个‘假’神仙嘛!天意你晓得?活见鬼,我就死活不信你!”
贾士芳笑道:“我为这里是不得已。也知道下场不好,也只好随遇安之而已。我劝三爷,您万万当心,不要玩聪明了,帝位没有您的。再玩聪明,什么也没有您的了。”
弘时像被烫了屁股,弹簧一样跳起身来,审视着贾士芳,良久,格格一笑道:“道士,我也劝你安分一点。捣鬼弄术不过巫师神汉的伎俩,摆不到大雅之堂上。
别以为你在皇上跟前得用,忘了自己身分根本儿,祸不旋踵!”“我是个小人物,原本就无足轻重。”贾士芳道,“过去恃强好胜,得罪了师门,也得罪了不少本领高强的异能之士。我没了那把木剑,现在不能回江湖了,在这里应付些琐碎事情,还是绰绰有余。
三爷,君相之命系于天,不系于鬼,十三爷是命数已尽,我也救不了他。把你神龛底下压的那张魇镇纸收了吧,它只会害你自己,真的,听我良言没有坏处!”
“你是说我害皇上,害十三爷?!”
“对,还有弘历四爷!”
“证据呢?”
“在你心里!”贾士芳冷笑一声,“头顶三尺有圣灵,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你敢对天起誓没有那些鬼祟事么?”
弘时像被人抽干了血的一具僵尸,死盯着贾士芳。
弘历安排捕真凶“你为什么叫‘铁头蛟’,头格外结实么?”
“小人原名范江春,水里营生走得。江湖上有人损我,叫我‘泛江虫’。我嫌难听,有一次水里讨换一船瓷器,几个兄弟下凿子也没弄沉它,我一个猛子潜过去,在水底把船板顶了个大洞,从此有了这个名儿。”
这两句问答,都和弘历想知道追杀自己的主使人毫不相干。众人听得莫名其妙,正发怔时,弘历一叹说道:“江湖上尽有能人好汉,可惜了一念之差去走黑道。你身为大盗,能顾惜人家妇女名节,可谓天良未泯。你好生认承,是谁主谋造意,是谁串连江湖要取我性命?本王珍惜人才,少不得还你个出身。”
“谢王爷超生,”铁头蛟连连叩头,说道,“谁主使这事,我真的不知道。原来是黄水怪负责联络,说北京有个三王爷,要取一个仇人性命。银子出到三十万,说如果在黄河了当这事,分给我十万。
我想得这套富贵,从此洗手,就答应了。那王府的师爷见过三四次,有时他姓课,有时他姓王,后来又说姓谢。黄水怪失利,谢师爷骑快马去见我,叫我邀集山东好汉陆地截,送了我二百两黄金五万银票,说截下这一票再给二十五万,三十万也能商量。
结果在槐树屯和爷们遇上……事败之后李大人追得我紧,我就逃到北京。先去的诚亲王府,说没有这个人。后来又去三贝勒府,门上人说姓谢的死了。后来又来了个旷师爷,又说谢师爷没死,诓我进府。我看他不怀好意,趁着小解,从花园水榭子里潜水逃出来……实话实说,就是这么个情形过节,小人再不敢有半点欺瞒的。”
弘历听得心动神摇,双目发呆。尽管早已隐隐感到这位“三哥”是几年来身边怪事迭出的渊薮,一旦证实了,他还是深深震惊了;居然出资几十万两银子收买江湖黑道人物,穷追数百里,苦苦地要自己的性命!
想着弘时平素温存揖让彬彬有礼的模样,那带着恍惚神情莫测高深的笑容,弘历竟不自禁打了个寒颤……如今怎么处?
但若隐忍不言退让,又事关自己前途,身家性命,一旦弘时得志,雍正百年之后,自己想做个弘昼那样的安乐公也是妄想。他咬牙思想着,已是拿定了主意,冷笑道:“我已经让他多次了,杀人可恕,情理难容——有这个虎狼心肠的兄弟,为君为臣,都是个不得安宁。”
他狞笑着看了看吴瞎子和铁头蛟吩咐道:“起来吧。话说透了,我们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不除掉后患,我就抬举你们,也架不住别人整治你们,要想清楚这个理儿!”
“四爷,您的意思我明白。”吴瞎子道,“江湖上头争个堂主会主,都投着下药打翻一锅汤呢!何况这大的花花世界?有什么吩咐,您只管说!”“说不上完全是我的事,与你们也不少相干。”
弘历的目光幽幽闪动着:“现在不拿到那个旷师爷,说不清楚河南这事情,河南的案子悬着破不了,李卫总有一天也吃挂落。此番我要斩草除根,你们助我一臂之力,擒旷师爷的事就落在你们头上。”吴瞎子怔了一下,说道:“他要躲在三爷府不出门,活捉只怕难。”
弘历一笑,说道:“只能活捉。姓旷的手里走了这位铁头蛟,他就得防着自己是第二个谢师爷叫人家灭了口,我断他宁肯逃出去再不敢还呆在三爷府。这个人交给你们两个,办法你们去想。”铁头蛟嘻嘻笑道:“我晓得,姓旷的在南市胡同养着个李大姐。咱们那里捂着他,准成!”吴瞎子笑道:“那今晚咱们掏他的窝儿去!”
…………
雍正披露弘时罪恶——弘时之死一夜之间,弘时由王爷就成了囚徒。他懵里懵懂被家人叫进来,说有大人夤夜来拜,睡眼惺忪到西花厅“接见”图里琛。没等他发问,图里琛就向他宣布圣命:“着图里琛前往密查皇三子弘时家产,并将弘时暂行密囚。”
多余的话一个字也不说,弘时便被九门提督衙门的人用八人大轿严严实实送到了畅春园风华楼西边一处闲置多年的小院落里。从文绣幔帐,宝鼎兽炭,一大群丫头老婆子太监拱着的王府中,突然跌落到这冷清凄凉的土壁房中,他才清醒过来,那一夜的惊心场面并不是梦。
他抱着双膝孤零零坐在烧得暖烘烘的炕席上,靠在墙上只是冥思苦索:到底哪里出了毛病?然而心里像泼了一盆浆糊的乱丝,无论如何理不出头绪来:张廷璐一案已是死无对证。
凭着张廷玉的小心翼翼,就是有什么证据,决不敢事过多年突然举发。隆科多当然恨自己,但他手中没有证据。
他不过是一条囚禁了的疯狗,谁会相信他狺狺狂吠?隆科多擅自带兵进驻畅春园,搜查紫禁城,都是借手允禩命令他干的。
允禩既死,连最后的证人也没有了,他怎敢攀咬自己这个身居九重之侧的管事阿哥?那么,是追杀弘历?主持这事的谢师爷已经灭口,就算捉到几个江湖匪豪,能凭他们含糊不清的口供定自己的罪?
巴汉格隆行法魇镇雍正,他原本不同意,后来旷师爷力劝,说“不管皇上藏在乾清宫匾后的遗诏传位给谁,三爷您在韵松轩,掌握了中央机枢权。只要事发突然,乱中有意为之,谁也替不了您!”结果更奇,一个神通广大的蒙古活佛,竟在雷霆大震中被摄得无影无踪,死在金水河畔!……
但旷世臣并没有被捕过,白天还在书房帮自己看稿子,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告发自己?……
在难熬的岑寂中暮色降临了,军士送进一枝白烛,又给弘时换了一壶热水,掩门退了出去。随着几声细碎的金属碰撞声,一切又归寂然,只远处偶尔传来上夜人悠长凄凉的吆呼声:“宫门——下钥,下千斤,小心灯火——啰!”
弘时挪动着麻木的身躯,就着开水吃了两块点心,觉得心里好受了点,既然事到临头,又想不出什么结果,且就听天由命吧!他拉过一块毡,在炕头叠了个枕头,拽过一床毯子,正要和衣卧倒,门一响,雍正已经进来,图里琛拿着钥匙站在他身边。
“你出去。”雍正对图里琛说了一句。回转身来,用一种难以描绘的神情看着弘时,一时没有说话。弘时的脸色苍白得厉害,似乎稍微受一点惊吓就会昏晕过去。眼睛绿得发暗,在微陷的眼窝里,幽幽闪着鬼火一样的光。
弘时早已坐直身子,用惊愕的目光盯着父亲,恍惚如对噩梦。半晌,才伏下身去叩头道:“儿臣无礼,因为儿臣都糊涂了,浑如身在梦境,既不知身在何处,也不知怎么来的……”
不知怎的,他的声音发颤,身子也在不停地抖动。雍正似乎迟疑了一会儿,说道:“你起来,坐着说话吧。”说着自盘膝坐了炕上。
弘时听雍正口气并不严厉,甚至还带着平日少有的温和,心里略觉放宽,叩头起身,在靠门小杌子上坐了。便听雍正干涩的嗓音问道:“听你的口气,并不知罪,且是很委屈,是吧?”
“是,儿臣确实不知道是怎么了。但雷霆雨露,皆是浩荡皇恩,儿子只想知道原因,并没有怨尤之心。”弘时愁眉苦脸,顿了一下,又道,“儿臣生性不如弟弟们聪敏,办差或有失误,但自问敬上爱下,没有使过黑心!”
“没有?!至今你居然还敢如此大言不惭!”雍正的火顿时被他撩起,腿一动就要下炕,却又自制住了,用冷得发噤的语气问道:“八王议政一案,你充的什么角色?你和允禄十六叔都说了些什么?还有永信、诚诺!陈学海你接见没有,说了些什么?”
弘时先听“八王议政”还觉得这是陈年老账,虽然心慌,并不惊悸,见雍正摆出了自己密地接见的人,才知道这件事情也不小。脸上顿时一红一白,期期艾艾说道:“时日久了,儿子记不清爽……”
雍正一口截断了他的话,说道:“‘祖制就是八王议政,闹一闹给万岁提个醒儿也不是坏事。’可是你说的?还有,说‘先帝和当今都是圣明天子,万一后世出了昏君,有个八王议政,能主持废立的事,于江山社稷还是有好处的!’”
弘时没想到这最隐秘的话,也都给人兜了出来,顿时背若芒刺,硬着头皮说道:“这是儿子当时一点蠢想头,想着恢复祖制是堂堂正正的事,圣躬独裁,遇上明主还好,遇上昏君就会坏了江山。皇上不说,儿臣至今还没有觉得错误……”
“巧言令色!”雍正沉闷地说道,“你和朕打马虎儿!你私调他们进京,又调唆他们这些话,睿亲王不和你们串连,你就安排他远远住到潞河驿。你心心意意怕弘历立太子,自量德力不够,要控制八王,亲掌上三旗,坐定了摄政王地位和弘历平分秋色!你妒忌弘历,是么?”
“没有没有!”弘时仰脸看着雍正,慌得连连摆手,“儿子纵不肖,怎么会妒忌弟弟?”
“不妒忌?”雍正冷冷说道,“既不妒忌,你告诉朕,那个姓谢的师爷现在哪里?他到河南山东几处地方都做了些什么?”
弘时惊恐地望着雍正,又躲闪着雍正刀子一样的目光,两只手下意识地死死攥住了小杌子,好半日才道:“阿玛这话我听不懂。我府姓谢的倒是有一个,发痧死了……”
“只怕不是发痧!”雍正的声音嘶哑中带着沉闷,像是从一只坛子里发出的声音,“他联络匪盗,两次堵截追杀弘历,事情不成功,自然是要灭口的——你不要忙着申辩。
你那个旷世臣,生恐当了谢师爷第二,昨天下午偷盘了你一处当铺款要逃,已被图里琛拿住。他没有你嘴硬,连同你魇镇朕和弘历的法物,连同你勾结巴汉格隆图谋要你阿玛的命,都招了!”
“这一定是弘历!”弘时突然绝望地叫道,“他见我主持韵松轩政务,心生妒忌,设陷害我!”
“算了吧!”雍正冷笑道,“演这个像生儿有什么意思?弘历替你开脱说情,你倒攀咬他,你可真是个大好人!你怕隆科多揭发你下令闯宫的事,所以你叫他背土布袋。
你怕阿其那情急把你的丑事张罗出来,所以遣散他的家人,故意不给他治病!宁肯让你的皇阿玛背上屠弟杀功臣的恶名——”
他陡然间提高了嗓门,“你可以算作个人?!上苍白给你披了一张人皮!夫人有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镜子,你照照自己的形容儿,可有半伦一伦?
张廷璐受你之托科场行奸,事情败露处刑腰斩,你整日围着朕,连一句减刑的话也不曾说。像你这样的东西,作恶事坏事也是毫无章法,哪个人跟着你不要留一手?哪个人肯替你出力卖命?”
弘时浑身已经瘫软下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杌子上溜跪到地下,直到雍正说完,他都像听着天上的雷,一声一声沉重地打击着他本来已十分衰朽脆弱的心。
他张皇四顾,似乎在寻着什么可以依靠的东西,但这屋里,除了那枝闪着一幽一明的光的蜡烛和一个毫不动情的皇帝,什么也没有。
半晌,他忽然无望地发出狼嚎一样的悲啼,边哭边叩头,说道:“皇阿玛圣明,皇阿玛圣明……那都是冤枉的……您从小儿看着儿子长大。儿子虽然愚顽不肖,作坏事的心胆是没有的……”
“朕半点也不‘圣明’。”雍正看也不看弘时,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杀张廷璐,你一句话也没说,朕只是觉得你‘忍’。他的事朕过后有疑惑也有所不忍,所以自他之后,朕废除了大清律里的腰斩之刑,也为恕自己的心。
八王议政,朕只是觉得你暧昧,心地阴暗,想和这群污糟猫王爷分一杯羹。隆科多搜园,朕对你已经十分警惕,还想着你毕竟是儿子,能包容就包容了,也许是你不掌权,想着好比一只狗,喂饱了也就不咬人了。孰料你进而要杀人,杀你的父亲,还杀你的弟弟。你可以说是古今天底下最贪恣暴虐的衣冠禽兽了!”
弘时向雍正爬跪了几步,悲号道:“皇阿玛,皇阿玛……您是儿的父亲,那些事……有的有,有的没有……你不要听信外人谗言……”
“你也是读过书,受过明师指点教诲的,”雍正一脸鄙夷的神气,继续说道,“岂不闻杀人可恕情理难容?你身为皇阿哥,万岁之侧千岁之体,若不为非,哪个敢来动你,又有谁敢来离间父子之情?
朕若证据不足,又焉肯将你夤夜捉拿到此?朕若无情,又焉能不把你交部严议明证典刑!”“皇阿玛!您听我说……”弘时的精神堤防,在雍正排炮一样的轰击下突然崩溃了。
他像一座受潮的糖塔,委顿着软瘫在地,说道:“……总归可怜儿子糊涂,听了下头人调唆,以为……以为除掉了弘历,儿子……占定嫡位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有魇镇的事……河南追杀弘历……那是他们办过了我才知道,并不是儿子生谋造意……阿玛……您要把我交部议罪么?……啊?您说话呀……”
雍正听他哭得凄惶,一股又酸又涩的口水涌上来,眼泪已夺眶而出。他像石头人一样站在当地,听着弘时撕心裂肺的哭声,突然想起那年承德事变,太子允礽和十三阿哥允祥被囚,狮子园里一片恐怖,奶妈子抱着刚满两岁呀呀学语的弘时逗自己开心的往事。
又忆到让弘时骑在自己脖子上去捉爬在树干上的蝉,尿了自己一身……雍正不禁长叹一声。
他用沉缓的语调说道:“朕瞧不起你这模样,大丈夫死则死耳,作得出就当得起,你起来!”
“是!”弘时爬起身来,已是额青眼红,畏缩地又坐回小杌子上,说道:“请父亲训诲……”“你弑父杀弟,欺君灭行,依着《大清律》,除了凌迟,没有第二条刑罚。”
雍正幽然说道,“朕思量,把你交部,又是哗然天下一件大案,不但你死,还要带累多少人,家丑也外扬了。所以朕一开头就是密地捕你,为的不招众议。”
弘时用感激的目光看着父亲,低声说道:“谢父皇成全呵护恩典。”雍正也看着这个不成器的儿子,从心底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走下炕来,背对着弘时,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你知恩就好!你的罪犯在十恶,断无可恕之理,但朕与上书房军机处等人商计,不能把你交部显戮。一是国家禁不住大案迭起,二是朕也觉得丢不起这个人。”
“那——皇阿玛打算——圈禁?”
…………
“到岳钟麒军中……效力恕罪?”
雍正依然摇头,说道:“没法给你判,没法给你身分,你到军中没有名目。”
“那么儿子只有削发为僧,在佛前忏悔赎罪了……”
雍正倏地转身,灯影里看不清他的神色,只听语气深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你还是尽想着活命之道!凭你这身份,哪个庙藏得住你?你借忏悔之名求生活命,不怕有一日暴露,让你伤透了心的老阿玛再蒙羞耻?且不说你的罪没法恕,就是可恕,你的心可恕么?既然你自己不愿想,朕就替你说,你除了自尽没有第二条可以恕心谢罪的路!”
“皇阿玛!”弘时顿时吓得泪流满面,“唿”地跪直了身体扑上前,紧紧搂住雍正双膝,摇撼着,哭泣着,说道:“儿子有罪当死……原没有可辩之处……念起皇阿玛子胤单薄,儿臣一死不足惜,带累孙子都是有罪之人,宗室近亲更是零落……”
“你此刻才想到‘宗室’?晚了!”雍正见他一副苦乞命相,心中更增反感,冷冷说道:“朕不想和你纠缠,你这副可怜相打动不了朕!一条是你今夜从速自尽,朕念父子血胤相关,关照你的家人子女不受株连,给你一个小小处分塞了众人耳目。
一条你就这么挺着,朕自然将你的罪名证据一并发给大理寺刑部议处。他们若肯饶你,朕不加罪。他们不肯饶你这人神共愤的逆子,朕只有依律处置,绝无宽贷之理!因为朕已经加恩,亲自来劝,你不受这个恩!”
他的语调变得异常沉痛,“虎毒不食子,朕何忍置你于死地?但你细想,活着有什么面目见朕,你又怎样见你的弘历弟弟?你又怎么样面对你的妻儿?如何周旋于王公大臣之间?不但你,连朕也羞得无地自容……
但你若自尽一死之血可以洗清你的罪,世人怜你是作得当得的汉子,不至于让你的家人再蒙羞辱……儿子,你……你自己思量吧!”他后退一步,挣开弘时的双手,拖着深重的步履出来,对守在的图里琛说道:“给你三爷把东西预备好。抬一桌酒席,要丰盛些!”
图里琛身负雍正安全,一直紧靠门站着听里边动静,父子二人的对话听得明明白白。他心里也是紧缩了一团,恍惚迷离半日才回过神来,躬身道:“喳!奴才遵旨!”看了看屋里半晕半瘫伏跪在地的弘时,忙着便去为他张罗绳子、刀和药酒。
弘时没有谢恩,也没有再说一句话。
……
君臣、父子、夫妻,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的教义是维护封建社会运转、维持国家、家庭稳定的基石,而弘时的所作所为已经失去了一个臣、人,基本的礼义廉耻。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自以为做得巧,殊不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雍正杀弘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虎毒不食子,雍正杀弘时是为了帝国的稳定,是为了家国的未来。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