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马之谜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马匹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和战争利器,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卢马"这一名称频繁出现在古籍文献和民间传说中,却鲜有人能准确指出它究竟是谁的坐骑,卢马究竟是何方神圣的专属坐骑?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牵涉到中国古代马文化、历史人物评价以及文学艺术创作等多个层面,本文将从历史记载、文学典故、民间传说等多个角度,深入探讨卢马的身份之谜,揭示这匹神秘坐骑背后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
卢马的历史溯源
"卢马"一词最早可追溯至汉代文献,但其具体指代却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记载:"项王骏马名骓,常骑之。"有学者认为这里的"骓"可能就是后世所称的卢马的前身,因为毛色描述相似,东汉时期,《说文解字》对"卢"字的解释为"黑色",因此卢马最初可能泛指毛色深黑的良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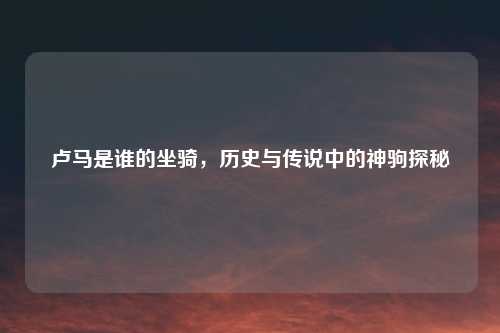
到了三国时期,卢马开始与特定历史人物联系起来。《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记载:"吕布有骏马名曰赤兔,又号卢马。"这段文字首次将卢马与吕布联系起来,但同时也造成了混淆,因为赤兔马以红色著称,与"卢"字的黑色本义相矛盾,这一矛盾暗示着"卢马"的称谓可能已经超越了单纯毛色描述,成为一种尊称或美称。
唐代是中国古代养马业的鼎盛时期,卢马的形象也更为丰满。《唐会要》详细记载了宫廷御马中的"六闲卢马",表明此时卢马已成为一种特定品种或等级的代称,杜甫在《高都护骢马行》中写道:"腕促蹄高如踣铁,交河几蹴曾冰裂。"虽未直接提及卢马,但描述的骏马形象与后世卢马的特征高度吻合。
宋元以后,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卢马的形象逐渐艺术化和符号化,苏轼在《赤壁赋》中提及"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虽未点明卢马,但反映了宋代文人对名马的审美标准,这些标准后来也被用于塑造卢马的文学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永乐大典》中收录的《马政》篇详细记载了历代名马,卢马位列其中,但对其归属仍语焉不详,为后世留下了谜团。
文学典故中的卢马形象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长廊中,卢马的形象被不断丰富和艺术化,成为文人墨客寄托情怀的重要意象,唐代诗人李贺在《马诗二十三首》中写道:"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虽未直言卢马,但其笔下的神骏形象与传说中的卢马气质高度契合,李白在《将进酒》中"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豪迈诗句,也被后人联想为对卢马等名驹的礼赞。
元代杂剧对卢马的形象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关汉卿在《单刀会》中描写关羽坐骑时,虽以"赤兔"相称,但舞台表演中马的颜色处理常偏向深色,无形中与卢马的形象产生交融,这种艺术处理使得卢马与赤兔马在后世民间认知中经常被混为一谈,明代小说《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对吕布坐骑的描写尤为精彩:"那马浑身上下,火炭般赤,无半根杂毛;从头至尾,长一丈;从蹄至项,高八尺;嘶喊咆哮,有腾空入海之状。"这段文字虽标明是赤兔马,但其雄伟形象也成为后世塑造卢马的重要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卢马在文学作品中常常被赋予超越普通坐骑的灵性。《太平广记》中收录了一则关于卢马的异闻:某将军战败被困,其坐骑卢马夜间独自穿越敌营,引来救兵,这类故事强化了卢马通灵性的文学形象,使其成为忠义与智慧的象征,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马骥》篇中,更是将神马的形象推向极致,虽未直言卢马,但其中关于"龙马"的描写明显吸收了卢马传说中的诸多元素。
在诗词歌赋中,卢马常被用作怀才不遇的隐喻,辛弃疾"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词句,表面上描写战场景象,深层则寄托了报国无门的愤懑,这里的"的卢"是否就是卢马虽存争议,但两者在文学意象上的相通性显而易见,卢马在文学中的这种多重象征意义,使其超越了单纯的坐骑身份,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民间传说中的多元解读
民间传说为卢马的身份之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解读版本,这些口头文学虽缺乏历史严谨性,却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历史人物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在河北、山东一带流传的民间故事中,卢马常被描述为关羽的坐骑,一则广为流传的传说称:关羽败走麦城时,卢马流泪跪地,不愿主人独自赴死,最终随关羽一同殉难,这个凄美的故事将卢马塑造成了忠义的化身,与关羽的民间形象高度契合。
然而在山西、陕西等地的传说中,卢马又常与吕布联系在一起,当地民间艺人演唱的鼓词中描述:吕布被曹操围困下邳时,卢马夜渡护城河,往来传递消息,这类传说突出了卢马超凡的水性和耐力,同时也反映了民间对吕布勇武形象的某种认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传说中,卢马常被赋予预见灾祸的能力,如在吕布被擒前会不安地嘶鸣等细节,体现了民间文学对动物的神化倾向。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卢马则有独特的解读,彝族史诗《铜鼓传》中提到,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时,骑乘一匹名为"卢"的神马,此马能踏云而行,日行千里,苗族古歌中也有类似记载,将卢马描述为能够沟通天地的灵兽,这些少数民族传说将卢马与诸葛亮联系起来,反映了边疆民族对三国历史人物的独特认知。
特别有趣的是,江浙一带的船民传说认为卢马其实是孙权的坐骑,一则渔民中流传的故事称:孙权巡视水军时,卢马能在船板上如履平地,展现了非凡的平衡能力,这个版本虽然缺乏历史依据,但体现了水上居民对历史叙事的重新诠释,综观这些多元的民间传说,卢马似乎成为了一个"万能符号",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都将自己推崇的历史人物与之关联,通过神化坐骑来彰显主人的非凡。
历史人物的坐骑考证
回到历史考证的层面,卢马的真实归属问题需要严谨的史料分析,陈寿《三国志》中确有吕布"常乘赤兔马"的记载,但并无"卢马"之称,裴松之注引《曹瞒传》提到"又号卢马"的说法,可能是后世对吕布坐骑的别称,史学家田余庆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中指出:"汉末三国时期,良马多有别名,赤兔、的卢、绝影等皆一时之选,后人常混为一谈。"这种混淆在唐宋时期已相当普遍。
关羽坐骑的史料记载更为模糊。《三国志》仅提到关羽斩颜良时"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未言明马匹名称,元代郝经在《续后汉书》中首次将"的卢"与关羽联系起来,但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后世附会,历史学家方诗铭考证指出:"'的卢'原为刘备坐骑,见《三国志》裴注引《世语》,记载刘备避樊城之难时'所乘马名的卢',后人因关羽形象高大,渐将名马事迹移植其身。"
赵云坐骑在正史中几乎没有专门记载,但民间却普遍相信他骑的是白马,这种认知主要源于《三国演义》的艺术塑造,书中描写赵云"白袍白马",长坂坡单骑救主的情节深入人心,考古发现的东汉末年陶马俑显示,将领坐骑颜色多样,并无严格规定,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的铜马饰件证明,黑色战马在当时确实备受推崇,这可能就是"卢马"称谓流行的物质基础。
关于诸葛亮坐骑的史料更为稀缺,因其主要身份是文官而非武将。《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出入常乘素车",即没有华丽装饰的车驾,符合其清廉形象,云南昭通出土的东汉"骑马诸葛亮"画像砖虽被当地宣传为证据,但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后世追崇之作,不足为凭,综合史料来看,卢马最可能原指刘备的"的卢马",后在文学艺术发展中逐渐成为多位英雄共享的文化符号。
卢马的文化象征意义
卢马作为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符号,其象征意义远超过一匹普通坐骑,从色彩象征来看,"卢"字的黑色本义使卢马与中国古代的北方、水德等概念产生关联。《周易》将黑马归为"坎"卦象征,代表险阻与智慧,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卢马在传说中常具有预见危险的特异功能,东汉谶纬之学盛行时,黑马被视为祥瑞,《宋书·符瑞志》就有"黑龙马见,圣人出"的记载,这种观念为卢马的神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军事文化角度看,卢马代表了古代中国对战马的极致追求,汉武帝为获取大宛汗血宝马不惜发动战争,可见良马在统治者心中的地位。《唐六典》将战马分为上中下三等,卢马显然属于最上等的"龙种",宋代《武经总要》详细记载了良马的标准:"头欲得高峻,骨欲得圆而粗,耳欲得小而锐,目欲得大而光",这些标准与文学作品中卢马的形象描述高度一致,卢马因此成为古代军事力量的象征,体现了冷兵器时代骑兵的至高地位。
在伦理道德层面,卢马被赋予了忠义品格,中国传统文化常通过动物来喻人,如《忠经》就有"犬马之诚"的说法,卢马对主人的不离不弃,在民间故事中常被用来反衬人的背信弃义,元代杨维桢在《铁崖乐府》中咏卢马:"人间多少负恩者,不及将军一匹马",直指世态炎凉,这种道德投射使卢马成为儒家伦理的特殊载体,其形象中凝结了中国传统价值观。
从审美维度看,卢马体现了中国古代对力量与优雅的独特理解,杜甫《房兵曹胡马》中"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的描写,代表了文人对骏马的审美理想,宋代画院考试常以"踏花归去马蹄香"为题,要求表现马的轻盈灵动,卢马在艺术作品中往往被塑造成力量与优雅的完美结合,这种审美取向影响了中国绘画、雕塑中马的形象塑造,形成了独特的"龙马精神"美学传统。
卢马的文化归属
经过多方面的考证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综合性结论:卢马并非专属某一位历史人物的坐骑,而是在文化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复合型象征符号,从历史本源看,它可能与刘备的"的卢马"关系最近;从文学影响看,它与吕布、关羽的形象深度交融;从民间接受看,它又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文化内涵,这种多重归属恰恰体现了中国文化"层累地造成历史"的特点,不同时代、不同群体都将自己的理解和情感投射到卢马这一形象上。
卢马是谁的坐骑?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或许是:它是中华民族集体想象中那匹永远奔腾的骏马,承载着我们对力量、速度、忠义和智慧的向往,从司马迁笔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感慨,到今天"龙马精神"的励志口号,卢马已经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指涉,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永恒的精神符号,解开卢马身份之谜的过程,实际上是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解码,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历史如何被记忆、被诠释、被赋予新的生命。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